制造業(yè)或成中資對(duì)美并購(gòu)新機(jī)遇
綜合比較中美在人工、能源、資金、物流、供應(yīng)鏈以及稅收等方面的成本,總體而言中國(guó)較美國(guó)仍占有比較優(yōu)勢(shì),但差距在縮窄。制造業(yè)不同子行業(yè)由于成本構(gòu)成及銷售對(duì)象不同而可能在美國(guó)生產(chǎn)更有優(yōu)勢(shì)。

中美制造業(yè)并購(gòu)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挑戰(zhàn)。美國(guó)方面,政府對(duì)高端制造業(yè)的收購(gòu)審查仍有諸多限制,國(guó)內(nèi)就業(yè)保護(hù)強(qiáng)化,特朗普新政的具體推行也面臨很大不確定性;很多中西部制造業(yè)利潤(rùn)率不高,本土化生產(chǎn)盈利前景不樂觀。中國(guó)方面,短期內(nèi)外匯管控政策趨嚴(yán),且經(jīng)過近年海外并購(gòu)熱潮,杠桿率攀升與投后整合消化也制約著企業(yè)海外收購(gòu)的步伐。
中美制造業(yè)并購(gòu)面臨戰(zhàn)略性機(jī)遇與挑戰(zhàn)
美國(guó)在金融危機(jī)后的奧巴馬時(shí)代即實(shí)施了制造業(yè)復(fù)興計(jì)劃——通過發(fā)展先進(jìn)制造業(yè),占據(jù)技術(shù)的制高點(diǎn),其著力點(diǎn)在于高科技清潔能源產(chǎn)業(yè)、生物工程、航空航天、納米技術(shù)等。特朗普也將重振制造業(yè)作為一項(xiàng)核心政策主張,但其著眼點(diǎn)在于提升就業(yè),承諾把流向海外的制造業(yè)就業(yè)機(jī)會(huì)重新帶回美國(guó)。兩相對(duì)比,前者由于美國(guó)政府對(duì)高端技術(shù)領(lǐng)域的審查保護(hù),中國(guó)企業(yè)很難參與其中;而后者由于在就業(yè)和資金方面的較強(qiáng)訴求以及非核心高端領(lǐng)域的相對(duì)側(cè)重,為中國(guó)資本提供了參與可能。
對(duì)中國(guó)制造業(yè)來(lái)說(shuō),內(nèi)外驅(qū)動(dòng)因素使其處于升級(jí)轉(zhuǎn)型的關(guān)鍵路口,海外并購(gòu)需求迫切。外部因素令中國(guó)制造業(yè)大而不強(qiáng),面臨發(fā)達(dá)國(guó)家制造業(yè)復(fù)興“高端回流”與低成本發(fā)展中國(guó)家“中低端分流”的前后夾擊;內(nèi)部則面臨人口紅利消失、經(jīng)濟(jì)轉(zhuǎn)型以及需求升級(jí)的倒逼。
所謂“高端回流”,即美、日、歐等發(fā)達(dá)國(guó)家關(guān)注創(chuàng)新、網(wǎng)絡(luò)化、智能化、再制造、服務(wù)型制造等,大力發(fā)展機(jī)器人、3D打印、新能源汽車等先進(jìn)產(chǎn)業(yè),試圖重塑制造業(yè)競(jìng)爭(zhēng)新優(yōu)勢(shì)。如美國(guó)的先進(jìn)制造業(yè)回歸計(jì)劃;德國(guó)的工業(yè)4.0 戰(zhàn)略;日本的機(jī)器人產(chǎn)業(yè)革命。
所謂“中低端分流”,即“中國(guó)制造(Made in China)”的低成本優(yōu)勢(shì)正在被亞洲等新興國(guó)家追趕。如巴西工業(yè)強(qiáng)國(guó)計(jì)劃推出擴(kuò)大市場(chǎng)規(guī)模、增加產(chǎn)品出口多元化的各種措施;印度全球推銷“印度制造(Made in India)”,重點(diǎn)在于改善商業(yè)環(huán)境、增加投資吸引力,提高制造業(yè)就業(yè)水平,提高印度在全球制造業(yè)市場(chǎng)份額等。
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,中國(guó)的勞動(dòng)力成本上升迅速,綜合成本優(yōu)勢(shì)已不顯著,2015年中國(guó)勞動(dòng)生產(chǎn)率水平(7318美元)為世界平均水平(18487美元)的40%,相當(dāng)于美國(guó)(98990美元)的7.4%。與此同時(shí),需求端也面臨消費(fèi)升級(jí),與國(guó)內(nèi)結(jié)構(gòu)性的產(chǎn)能過剩形成矛盾,倒逼國(guó)內(nèi)的經(jīng)濟(jì)增長(zhǎng)模式由投資驅(qū)動(dòng)轉(zhuǎn)向消費(fèi),由低端粗放向高附加值轉(zhuǎn)變,倒逼制造業(yè)的升級(jí)轉(zhuǎn)型。
新格局下的并購(gòu)模式與方向
中美制造業(yè)比較優(yōu)勢(shì)的動(dòng)態(tài)演變
綜合比較中美在人工、能源、資金、物流、供應(yīng)鏈以及稅收等方面的成本,總體而言中國(guó)較美國(guó)仍占有比較優(yōu)勢(shì),但差距在縮窄。制造業(yè)不同子行業(yè)由于成本構(gòu)成及銷售對(duì)象不同而可能在美國(guó)生產(chǎn)更有優(yōu)勢(shì)。
人工成本:中國(guó)人工成本上漲快,但仍遠(yuǎn)低于美國(guó);不過在勞動(dòng)生產(chǎn)率方面,雖然中國(guó)增長(zhǎng)迅速,但仍顯著落后于美國(guó)。如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所言,美國(guó)藍(lán)領(lǐng)工資是中國(guó)8倍,白領(lǐng)是中國(guó)2倍多;又如根據(jù)波士頓咨詢(2014年數(shù)據(jù)),勞動(dòng)力綜合成本指數(shù)美國(guó)為18.2,中國(guó)為4.5。
能源成本:美國(guó)工業(yè)電價(jià)約為中國(guó)一半,天然氣價(jià)格約為1/3。對(duì)玻璃(能源占成本比重近一半)等高耗能行業(yè)來(lái)說(shuō)影響顯著。
資金成本:中國(guó)融資成本高于美國(guó)。
物流成本:美國(guó)相對(duì)占優(yōu)。美國(guó)沒有過路費(fèi)、過橋費(fèi);中國(guó)各種收費(fèi)較多,油價(jià)也偏高。
稅負(fù)成本:爭(zhēng)議較大。考慮到中國(guó)的隱性稅收成本以及制造業(yè)利潤(rùn)率較低,一般稅前利潤(rùn)率10%~15%的企業(yè)將增值稅折算成企業(yè)所得稅后的稅率近50%,高于美國(guó)的39%(聯(lián)邦企業(yè)所得稅+州與地方所得稅)。
供應(yīng)鏈成本:中國(guó)作為制造業(yè)大國(guó),過去幾十年形成了很強(qiáng)的集群和供應(yīng)鏈優(yōu)勢(shì)。
新格局下的并購(gòu)模式與并購(gòu)方向
在中美傳統(tǒng)比較優(yōu)勢(shì)下,常見的并購(gòu)模式主要有:市場(chǎng)換技術(shù)模式,中國(guó)生產(chǎn)+美國(guó)技術(shù)+中國(guó)市場(chǎng);前店后廠模式,中國(guó)生產(chǎn)+美國(guó)技術(shù)+美國(guó)市場(chǎng)(如萬(wàn)向在美國(guó)的收購(gòu));資源收購(gòu)模式,中國(guó)生產(chǎn)+美國(guó)資源;利用兩邊資本市場(chǎng)估值價(jià)差的并購(gòu)套利模式。
然而,當(dāng)前一系列政治經(jīng)濟(jì)因素的改變導(dǎo)致上述并購(gòu)模式面臨挑戰(zhàn)和改變。把握新形勢(shì)下并購(gòu)的“變與不變”,兼顧中美雙方所需,未來(lái)適應(yīng)新格局下的并購(gòu)模式將主要有以下三類:
就業(yè)換技術(shù)模式:美國(guó)技術(shù)+美國(guó)生產(chǎn)+國(guó)際市場(chǎng)。既可聯(lián)合國(guó)內(nèi)對(duì)等體量的國(guó)企民企對(duì)美收購(gòu),也可采取“批發(fā)零售”的模式,將美國(guó)大中型成熟企業(yè)按技術(shù)、品牌分拆出售給國(guó)內(nèi)相應(yīng)民營(yíng)企業(yè),幫助其升級(jí)壯大。兩種模式下都將保留甚至擴(kuò)大美國(guó)現(xiàn)有本土企業(yè)的生產(chǎn),但會(huì)將其技術(shù)和市場(chǎng)進(jìn)一步放大。
發(fā)展階段穿越模式:對(duì)于美國(guó)已成熟而缺乏增長(zhǎng)、但中國(guó)等新興市場(chǎng)仍處于需求快速增長(zhǎng)階段的某些制造行業(yè),收購(gòu)其中的美國(guó)優(yōu)質(zhì)企業(yè)嫁接后者市場(chǎng),如農(nóng)業(yè)機(jī)械、土壤、水環(huán)境治理企業(yè)。
資源收購(gòu)模式:美國(guó)資源+美國(guó)生產(chǎn)+中國(guó)市場(chǎng),如造紙企業(yè)對(duì)上游紙漿的收購(gòu)、棉紡企業(yè)到南卡收購(gòu)棉田等。
新格局下并購(gòu)模式的特點(diǎn)
“美國(guó)生產(chǎn)”是共同元素,挽救甚至擴(kuò)大美國(guó)成熟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的生產(chǎn)就業(yè),以滿足特朗普政府及民間的就業(yè)訴求,減小收購(gòu)阻力。
“技術(shù)”外延更廣,不僅指狹義的科技專利與優(yōu)勢(shì)研發(fā),還包括品牌、渠道、管理等,這對(duì)現(xiàn)階段中國(guó)制造業(yè)的升級(jí)換代同樣重要。因?yàn)楦母镩_放近40年,中國(guó)成為制造大國(guó),不少代工企業(yè)在技術(shù)方面已達(dá)到或超越美國(guó)水平(當(dāng)然很多先進(jìn)高端制造業(yè)領(lǐng)域仍有很大差距),但受制于品牌、售后服務(wù)管理以及國(guó)際渠道的差距,仍處于游兵散勇、無(wú)名英雄局面,急需提升層次品質(zhì)。這樣的升級(jí)將幫助國(guó)內(nèi)制造企業(yè):獲得品牌溢價(jià),提高利潤(rùn)率;提升品質(zhì)和市場(chǎng)份額,提高行業(yè)集中度,促進(jìn)行業(yè)整合;獲得美國(guó)及國(guó)際市場(chǎng)的客戶和銷售渠道,進(jìn)軍國(guó)際市場(chǎng)。
“全球戰(zhàn)略”是中國(guó)的著眼點(diǎn),制造業(yè)的升級(jí)換代瞄準(zhǔn)的是全球市場(chǎng)和生產(chǎn)布局。這是微觀上中國(guó)企業(yè)發(fā)展壯大的必經(jīng)階段,也是宏觀上推動(dòng)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和供給側(cè)改革的必然需求。一方面,通過收購(gòu)吸收美國(guó)的品牌渠道優(yōu)勢(shì),開拓美國(guó)及全球市場(chǎng)。這既有利于促進(jìn)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,而且對(duì)很多周期性行業(yè)來(lái)說(shuō),還可以緩解國(guó)內(nèi)的產(chǎn)能過剩,平衡不同國(guó)家的投資周期和對(duì)沖風(fēng)險(xiǎn)。另一方面,“美國(guó)生產(chǎn)”并不意味著放棄國(guó)內(nèi)的生產(chǎn),可通過整合國(guó)內(nèi)零部件生產(chǎn)降低成本,提升其本土競(jìng)爭(zhēng)力和份額;同時(shí)增量全球市場(chǎng)部分仍可根據(jù)比較優(yōu)勢(shì)放在國(guó)內(nèi)或全球布局。
參考上述關(guān)于中美成本對(duì)比與并購(gòu)模式的討論,并購(gòu)方向上可著重考慮以下幾類:
第一,擁有核心技術(shù)、品牌和渠道,利潤(rùn)率高的制造業(yè),如高附加值的汽車零部件企業(yè),品牌服裝、家電企業(yè)等。
第二,中國(guó)市場(chǎng)廣闊而美國(guó)市場(chǎng)相對(duì)缺乏增長(zhǎng)的優(yōu)質(zhì)成熟制造業(yè),如農(nóng)業(yè)機(jī)械、土壤治理等。
第三,人力成本占總成本比例小、資本或技術(shù)密集型制造業(yè),發(fā)揮美國(guó)比較優(yōu)勢(shì),如機(jī)械、化工、玻璃等資本品企業(yè)。
第四,資源豐富或擁有上游資源的制造業(yè),以幫助國(guó)內(nèi)企業(yè)實(shí)現(xiàn)垂直整合,如紙漿廠、雙匯對(duì)Smithfield的收購(gòu)等。

文章版權(quán)歸西部工控xbgk所有,未經(jīng)許可不得轉(zhuǎn)載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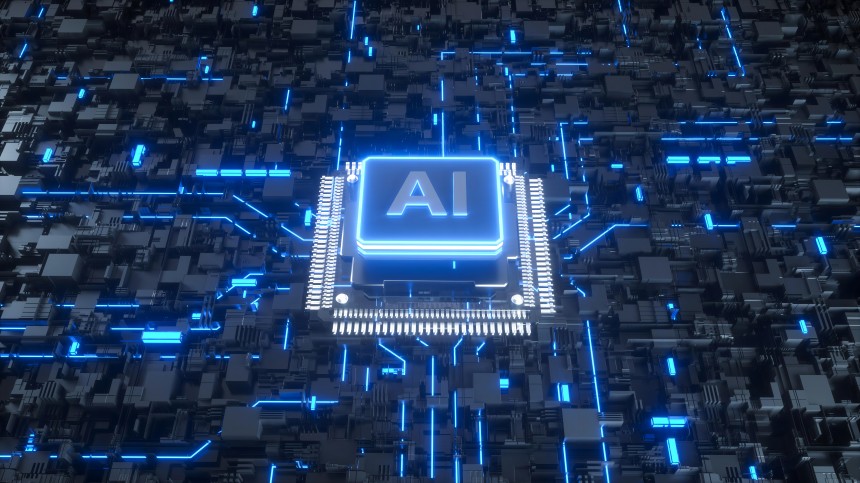

 服務(wù)咨詢
服務(wù)咨詢